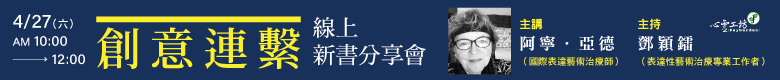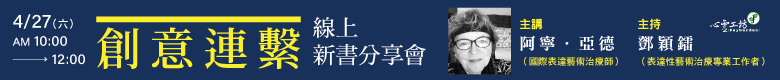|
【第二章】大團體心理學 1921年,佛洛伊德發表了論文〈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他並不認為人們單純地聚集在一起就叫做團體,而是將種族、國家、宗教或專業組織描述為團體。繼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 1895)關於團體心理的觀點之後,佛洛伊德關注的是個體在團體之中如何發展出新的經驗,比如失去獨特性、容易受到暗示等等。他把教會與軍隊進行了比較。雖然這兩種團體在許多面向迥然不同,但各自都有一個領袖人物(耶穌基督和總司令),以平等的關愛來統治和對待全體成員。團體的成員會將自己的領袖加以理想化,用佛洛伊德的話來講,因為他們「將同一客體放入他們的自我理想」,並「在他們的自我之中彼此認同」。
在更早期的一篇論文之中,佛洛伊德參考史前時代和現實之中從未觀察到的「原始部落」的概念,來描述圖騰崇拜和亂倫禁忌。在〈群體心理學和自我的分析〉之中,他將群體的形成與「原始部落」聯繫了起來,並寫道,群體的領袖正是「原始父親」。原始父親會阻止自己的兒子們滿足自身的性衝動。只有繼承者才有可能獲得性滿足。顯然,佛洛伊德的興趣在於,群體對個體而言究竟意味著什麼,而個體作為群體的一員又有何種表現。而如果成員之間共同的聯繫不復存在,就會引發恐慌。佛洛伊德還指出,群體的歸屬感會使群體成員對陌生人產生偏見。羅伯特.維爾德(Robert Waelder, 1936)則是最先提出,佛洛伊德描述的群體其實是退行的大團體。在本章的最後,我將會闡述大團體的退行。
從佛洛伊德開始,一些精神分析師就對大團體心理學產生了興趣。然而,和佛洛伊德一樣,他們主要還是關注大團體對個體的意義,比如伊底帕斯父親等等。在意識到孩子的心靈如果沒有與母親或養育者互動就不會進化之後,一些學者因此假設,群體成員會將他們所屬的大群體視為母性的自我理想,或是可以修復自戀受損的乳房母親(breast-mother)。然而,一直到了團體分析師(group analysts),才開始將焦點注重於社會文化因素對團體心理的焦慮模式所扮演的重要性。羅比.弗萊德曼(2008)指出,人們與他們形成的群集是相互關聯的。他還補充說道,夢想既是心靈與社會共同的創造物,也是心靈與社會的創造者。
在文獻資料之中,「團體」或「大團體」等術語一直都指涉著多種情境。例如,這些術語可以用於描述那些聚集在一起接受治療的人們;或來自不同種族背景的人們,聚集在一起討論彼此之間的差異;或描述專業組織或國家的成員。在本書的第一章之中,我闡述了我使用「大團體」這個術語時的含義,以及大團體心理學本身是什麼。
在本章,我會闡述與大團體心理學本身有關的概念,並舉例說明這些概念。這些例子源自於不同的國家和地區。
過去,當我描述由大團體引發的創傷性攻擊事件時,在某些情況下,我會收到一些同行的反饋。他們會向我表達失望的情緒,這些同行都是這些大團體的成員。他們覺得,我是在故意對他們的種族或國家認同發表侮辱性的言論。比如,我研究並發表了塞爾維亞在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領導之下所發生的事情,塞爾維亞的一位同行便一直指責我是塞爾維亞人民的公敵,因為我有土耳其背景。我曾經參與將土耳其具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軍隊和庫德人代表聚集起來,包括被監禁的庫德工人黨領袖阿卜杜拉.奧賈蘭(Abdullah Öcalan)的親密夥伴,尋求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土耳其境內所謂的「庫德族問題」。有人便嚴厲地指責我,說我與土耳其人作對,或與庫德人作對。首先,我想說明的是,人們和大團體兩者的攻擊性或力比多投入,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是一樣的;它們可能是「正常的」,或者有時候被嚴重地誇大了。我舉出我所研究的事件做為範例,以說明我從中得到的發現。但這並不意味我故意選擇某個特定的大團體來羞辱。其次,我始終都秉持著自己的精神分析身分來處理大團體衝突。我(或者我們團隊的其他成員)不會提出解決方案;我只是嘗試找到一些方法,幫助大團體的代表們自己想出解決的方案。
大團體身分認同
從長達數十年於國際場合的行動中,我瞭解到,在政治、經濟和法律議題等可見因素的背後,引發大團體衝突並使之持續存在的核心心理因素,乃是保護和維繫大團體身分認同。
在工作之際,我會聽到一些說法用以表達這種大團體身分認同的主觀體驗,諸如「我們是賽普勒斯土耳其人」、「我們是巴勒斯坦人」、「我們是立陶宛猶太人」、「我們是生活在愛沙尼亞的俄羅斯人」、「我們是克羅埃西亞人」、「我們是希臘人」、「我們是共產主義者」、「我們是遜尼派穆斯林」等等。
身分認同不同於可以被他人觀察和感知到的性格與人格;身分認同指的是個體內在的運作模式:感知並經驗到這個身分認同的人是這個當事者,而不是局外人。德裔美籍發展心理學家艾瑞克.艾瑞克森(Erik Erikson, 1956)將童年以來慢慢演變而成的個體身分認同的主觀體驗,定義為一種個體內在的相同感,同時又與其他個體具有某些共同特徵。印裔美籍心理分析師薩爾曼.阿赫塔爾(Salman Akhtar)寫道,內在相同性的持續感受,會伴隨著自體體驗(self-experience)在時間層面的連續性:過去、現在與未來被整合入一個讓個體記住、感受和期待的存在所構成的流暢連續體之中。他還描述到個體的身分認同如何與現實的身體意象以及內在的凝聚感聯繫起來,和獨處的能力和清楚自己性別的能力是有何關聯,與諸如國家、種族或宗教等大團體身分認同又是如何聯繫起來的。
個人歸屬於某一個大團體的身分認同,是人類存在的一部分。在部落、種族、國家、宗教和意識形態的層次上的大團體身分認同,是普遍存在於世界各地的。它們是有著共同起源、歷史連續性和地域現實的神話與事實,以及共同的文化、語言、宗教和意識形態因素,最後交融所產生的結果。環境之中的現有條件引導著孩童們,投身於這種或那種的大團體歸屬感。例如,出生於印度海德拉巴(Hyderabad)的孩子,在發展大團體認同時會特別關注宗教或文化問題,因為那裡的成年人根據宗教的歸屬,定義了他們主要的大團體認同:是穆斯林還是印度教徒。賽普勒斯的孩子,如果出生於賽普勒斯土耳其人和賽普勒斯希臘人激烈衝突的時期,他們便會吸收由種族或民族情緒所定義的較強勢的大團體認同,因為在這個世界角落的那一時刻,比較要緊的是一個人究竟是希臘人還是土耳其人,而不是在意一個人究竟是希臘東正教基督徒,還是遜尼派穆斯林。
有些孩子的父母分屬於兩個不同的種族或宗教大團體。如果這兩個大團體之間爆發國際衝突,這些孩子可能會出現心理問題,甚至成年之後亦然。蘇聯解體之後,在喬治亞共和國裡,喬治亞人和南奧塞提亞人之間的戰爭特別使「混血」後裔的個體感到困惑,心理層面也備受苦惱。在特蘭西瓦尼亞(Transylvania),羅馬尼亞和匈牙利通婚所生的孩子在這兩個大團體彼此敵意開始激化的時候,也有這樣的情況。
「自家人」的心理生物學潛能
最近幾十年的科學研究顯示,人類嬰兒的心靈是相當活躍的,而且在孩童生命的最初幾個月和幾年裡,存在著一種「自家人」(we-ness)和偏愛同類的心理生物學(psychobiology)
潛能。我必須補充的是,這種「自家人」有其侷限,因為嬰孩或者孩童的經驗是有限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孩童們開始能夠將自己的心智意象,與熟悉的他人(比如母親)意象區分開來,將兩種意象的不同面向,諸如愉快與不愉快的,或者力比多的和攻擊性的面向,加以整合起來。幼小兒童在二十四個月到三十六個月大的時候,對文化卅社會的放大器(amplifiers)—也就是只和某個特定大團體相關連的象徵和符號,不論具體或抽象—便會有所察覺了。
認同
當孩子能夠將自己的意象與親密他人的意象這兩者加以分離並進行整合的時候,他們便認同了這些重要個體身上一系列現實的、幻想出來的、受到寄望的或者令人恐懼的元素。這種認同還包括具體以及抽象的大團體身分標記,比如語言、童謠與其他文化放大器,還有宗教和政治信仰,以及歷史意象等等。很久以前佛洛伊德就已經指出,對孩童而言,父母象徵著更大的社會。這包括了孩童會認同父母以及其他重要人物對大他者(Others)的偏見,無論這些偏見是善意的,還是敵意的。
沉積
在「認同」的過程之中,孩童是主要的行動者,他們從周邊的環境之中收集意象、看法、偏見以及各種各樣的心理任務,並使得這些事物成為他們的一部分。孩童也會成為沉積意象(deposited images)的儲存庫,並且會發展出各種各樣的心理任務,來應對這些沉積下來的意象,他們應對的方式有可能是適應不良的,也可能是富有創造性的。在「沉積」的過程之中,正是孩童生活之中的成年人,潛意識地感到有需要將某些事物置入孩童的心靈。作為一個替代兒童,我自己的自體表徵除了包含我外祖母和母親內心關於我亡故舅舅的意象之外,也包括鄂圖曼時期與我同名的重要人物之意象,以及修復這個意象的心理任務。關於沉積,我在之前的作品中還列舉過其他的例子。
心理DNA
當成千上萬的兒童成為同樣或類似的沉積意象及心理任務的接收者,他們便開始享有共同的「心理DNA」。例如,經歷了敵對團體所施加的集體禍患之後,受到影響的個體會留下類似(儘管並不完全一致)的自體意象,上面留存著重大事件所帶來的創傷。許多個體會將這些意象沉積在孩子的內心,並交給他們諸如此類的任務:「為我重拾我的自尊」、「讓我的哀悼過程走上正軌」、「堅定信念進行報復」,或者「永遠不要忘記,永遠保持警惕」。儘管下一代的每一個孩童都擁有自己個別的身分,但都與同樣的巨大創傷意象有類似的連結,而為了應對這種創傷,他們也擁有了相似的潛意識任務。如果下一代不能有效地完成他們共同的任務(常常如此),他們會將這些任務傳遞給第三代,以此類推。這樣的狀況在成千上萬的人們之間創造了一個強大的隱形網絡。沉積,還包括針對陌生的大他者(陌生人),傳遞各種存有偏見的元素。
共同的偏見
勒內.斯皮茨(Renè Spitz, 1965)的研究告訴我們,嬰兒可以辨識出圍繞在身邊的面孔並非都是他們的養育者。斯皮茨將自己的發現命名為「陌生人焦慮」,這種焦慮在六至十二個月時達到高峰,它與「正常」偏見的啟動也存在關聯。亨利.帕倫斯(Henry Parens, 1979)提醒我們,偏見並不是與生俱來的。帕倫斯告訴我們,在正常的發展過程之中,每一個新生兒都會經歷某些強制性的適應反應,使得孩童傾向於發展出偏見,孩童便由此懷有了偏見。我提出的術語「適合外化的目標」(suitable targets for externalization),其所要描述的是,孩童們會整合自身未經修補的意象,在達到高峰時,他們會在經驗之中瞭解到其他大團體的存在,並發展出共同的偏見。
適合外化的目標
讓我們回到我在賽普勒斯的童年時代。請大家想像一下,三歲的我正在賽普勒斯的一個希臘農場旁邊野餐,那裡的豬滿地亂跑。再想像一下,我想要試著碰觸與撫摸一頭小豬。我那穆斯林的祖母一定會強烈反對我的行為。對土耳其穆斯林來說,豬是「骯髒」的。作為一個文化卅社會放大器,豬並不屬於土耳其大團體,牠屬於希臘人。三歲的時候,我仍然有一些未整合的自體意象和內在客體意象。此刻,在賽普勒斯的希臘農場,我找到了一個合適的目標,來放置我不想要的、受到嚴重汙染的、未整合的「壞的」自體意象及客體意象。因為我是穆斯林的孩子,所以我不食用豬肉,因此,具體來講,我外化到豬這個意象之中的東西,是不會被重新內化的。幾乎每一個賽普勒斯的土耳其孩子都會選擇相同的目標,他們便對陌生的大他者有了共同的預期(precursor),並投以相似的偏見。一個蘇格蘭男孩會慢慢意識到,蘇格蘭短摺裙或風笛與蘇格蘭人之間的聯繫。這些事物會成為他未整合的「好的」意象之儲存庫。而他與其他所有的蘇格蘭男孩共同有著這種經歷。
孩童會使用各種各樣的文化卅社會放大器,比如特殊的食物、旗幟的顏色、教堂、清真寺、猶太會堂、屬於他們大團體或大他者的英雄圖畫,將其作為合適的外化目標,來放置他們「好」和「壞」的未整合意象。複雜的思想、感知、情感以及關於陌生大他者的歷史知識,是很晚的時候才發展出來的,孩童們無法意識到,他們透過經驗瞭解到的大他者象徵,可以幫助他們迴避自身的客體關係所帶來的張力。
孩童一旦開始利用共同的適合外化的目標,他或她在經驗方面便開始放棄成為一個博學通才(generalist)。此刻的孩童,對於自身歸屬於某個特定的大團體便有了更為堅定的感覺,並更堅定地將自己與共同的陌生大他者區分了開來。我們每個人都有偏見,這些偏見有可能是無害的,但也可能由於所經歷的各種各樣生活事件而變得懷有敵意,甚至是惡意。當人們存有了惡意的偏見,一些個體便會殺死其他的人類。在此,我想強調的是,「適合外化的目標」這個概念指的是發展出共同的陌生人焦慮,並且在大團體的層次創造出共同的偏見。同樣地,共同的偏見可能會保持在無害的狀態,也可能會變得具有敵意或惡意。
第二次個體化
在經歷青春期通道的時候,個體會潛意識地回顧自己在童年時期對熟悉的大他者所抱有的依戀。這導致了青少年的「第二次個體化」。彼得.布羅斯(Peter Blos, 1962, 1967)認為,堅定的個人認同和性別認同感受會在經歷青春期通道期間變得明確而具體。我則要補充:在青春期,個體在童年時期發展起來的大團體認同,也成為最終的認同。
受到青少年期和成年期生活環境的影響—比如,個體在青春期晚期或成年早期的時候,移民至另外一個國家定居—個體可能會否認或壓抑他們對自己童年時期發展起來的大團體認同的投入,但是這種大團體認同還是會在陰影之中保持「鮮活」。作為一名自願移民者,我發展出了美國人的認同。然而,我還是可以意識到自己的賽普勒斯土耳其人認同。不論是自願或被迫的移民者,如果能夠發展出穩定的雙重文化觀,他們的生活會過得更為舒坦一些。
他者
艾瑞克.艾瑞克森提出一個理論,認為原始人之所以會身著動物的毛皮、羽毛或爪子,是想用這種方法來保護自己沒有耐受力的赤身裸體。在這些外在覆蓋物的基礎下,每一個部落或氏族開始發展出自己的共同認同感,以及認為單憑這認同就可以安置自己身分的信念。艾瑞克森認為,人類已經演化成為「偽物種」(pseudo species),比如部落或者氏族,表現得好像是獨立的物種一般。這種假設,在許多關於大他者的古代文獻和語言之中,可以得到支持。阿帕契印地安人認為他們自己是人(indeh),而其他所有人則都是仇敵(indah)(Boyer, 1986)。古代的中國人視自己為人(people),將大他者看作鬼(keui)或者「進行捕獵的鬼魂」。居住在巴西雨林的蒙杜魯庫人將他們的世界劃分為屬於人的蒙杜魯庫,和屬於帕里瓦特(pariwat,即敵人)的非蒙杜魯庫,但排除掉某些他們認為算是友善的鄰居(Murphy, 1957)。只將自身看作是「人」的大團體,我還可以舉出其他一些例子,比如蘇丹的丁卡人(Sudanese Dinka;這個群體的名字可以翻譯為「人」)、努爾人(Nuer;「原初的人」)和北極的尤匹克人(Yupik;「真正的人」)。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地拓展艾瑞克森的觀點。彼此鄰近的原始團體之間為了生存,必須爭奪領土、食物、性和物品。我們可以想像,這種競爭最終會承擔起較屬於心理層面的影響。物質的必需品除去其作為真正的需要之外,也在吸收或產生著心理意義,比如:競爭、聲望、榮譽、權力、嫉妒、報復、羞辱、屈服、悲傷和哀悼等等。其中一些物質必需品便發展成為大群體的文化卅社會放大器,如同一面旗幟或者一首歌謠那樣,而且與歷史記憶、宗教、共同的自戀和大團體認同聯繫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