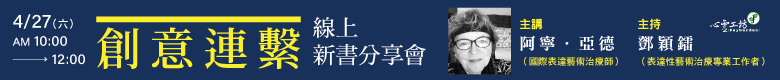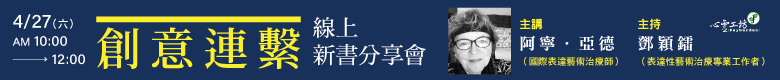|
心靈史的救濟 科學不斷往前推展,更新的文明創造了世界的秩序,
同時,也遠離了野地的力量和奧祕。
活在工具理性中的我們,能不能解除功利心態,
重返生命最原初的意趣?
坐在山裡,看著清澈的河水潺潺地流著,水面的紋路不斷地變幻著,枯葉在水面上打轉,薄霧在林間,如雲氣飄在樹葉上。
如此地把自己放在一片嵐氣之間,望著溪水,作為後工業時代的子民,我們感到「世界的失去」,與自然之間的對話,似乎在工業的技術興起之後,戛然停止。我們在電腦上與遠方的朋友通訊,我們的都市充滿了貨品,工廠不斷地製造電器與化學製品,而使我們遠離耕種的生活。這當然不是濫情的喟嘆,而是「世界的失去」。
如果我們翻一翻幾百年前的文字,會發現中國的文字歷史裡有許多詩歌吟唱,對於現代的人們來說,這詩人的快樂似乎令人費解,為什麼傳統的文字營造者願意創作這些詩歌,而我們又醉心於什麼?某種疏離似乎逐漸擴大,就像極地的臭氧層破了洞,我們心靈的趣味逐漸失去了興味,而電動玩具取代了人們之間的嬉戲,年節變得日復一日的無聊。
所謂「後現代」的處境正意味著某種人類對自己命運的決定:使用汽車來擠壓時空,使用電視節目代替人們之間的取樂,使用人工製品代替菜園的作物,使用圖片代替文字的閱讀,使用電子通訊代替見面──人類注定要活在人為的環境裡,人們用自己的手為自己舖路。
挑戰啟蒙,探求神話心靈
然而,這種後工業處境無法回頭。人為自己設下如此的處境並非一無所得,也不是有回頭路可以走,但是,人是可以反省的動物,他必須為自己所設下的處境負責,而且必須重新把自己的處境做個較好的反省,而構成後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界所謂的「歷史的救濟」(historical redemption)。「歷史的救濟」其基本涵義來自於人文社會科學界對人類歷史觀點的轉向,認為人類用自己的努力想完成的目標,不僅不必然是良善進步的,甚至是片面、不足為取的,人必須回頭把當初設想的生產目標、生活方式做徹底的反省,看看我們到底在歷史的哪一個環節出錯了,而謀思在出錯的地方重新設想,以扭轉人類的未來。
在這個世紀末,歷史救濟成為人文精神領域的「籌謀」,試圖在這精神日益異化的狀態裡,探尋人類人文精神領域的「重新活絡起來」。然而,這個工程極其龐雜,從生物界的基因危機到文學界的「解釋文學」,乃至環保運動、女性的人文革命,都在這股歷史救濟的運動裡頭。
在心靈史的歷史救濟方面,人重新發現了神話的心靈。神話的心靈重新被發現,有賴於各層面的學者。
學者努力往「原始文明」探求神話的心靈是一件很令人費解的事:人類好不容易從原始文明的愚昧掙脫出來,如何又返回原始心靈呢?那些原始社會流傳下來的神話充滿怪力亂神的傳說,荒誕不經的故事,又如何能夠開啟人類的智慧?而這些學者都是傳世的大師,到底他們心裡在想什麼東西,而我們卻懵懵懂懂呢?
這一切都必須從我們有文字與科技文明的歷史說起。在當今的社會,我們都把語言與科技視為歷史進步的動力,以為自從文字的歷史以來,人類才有文明;有了科技以後,人類社會有了更大的進步;這個觀點令我們深信,只有致力於文明的進步,人類的心靈才能獲得更完滿的睿智。
這種歷史文明進步觀卻備受挑戰。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人類的啟蒙世代遭受社會批判學者的質疑。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精神分析大師佛洛姆、人文政治學者漢娜?鄂蘭,都在人文心靈方面對啟蒙產生懷疑。法蘭克福學派的創始者麥克斯?霍克海默與特奧多?阿多諾在《啟蒙辯證法》中指出,啟蒙使人相信得到救贖,然而啟蒙思潮以理性、科學的推展,卻使人感受到更巨大的不幸。這個觀點,首先把人類歡唱的歷史理性打下了一個大問號。
這個疑問在五○年代提出,卻像滾雪球般地引發更多的迴響,姑且不論批判學派的後來發展,它卻為心靈革命開啟了一個里程碑。
解除文字魔咒,重返語言初始地
心靈歷史的救濟來自對語言的反省。過去,文字被視為心靈的指引者,但是,卻又是心靈的遮蔽者。
語言出現了的思維其實並不全然取代生命,但是人類用語言遮蔽了非語言的生命。如果用比較嚴重的話來說,語言是人類的另一種存有,而這種語言的存有性卻逐漸地褪去其與生命交合的中介處,而放逸到語言的疏離──人類將語言編織成一片自我欺騙的意識,使得語言不再與生命息息相關,語言成了被操縱之物:廣告、政治口號、訓話以及囈語。
語言與生命的交會處,正如本文一開頭所描述的山中流水。人坐在山中注視著流水,並不需要語言,但是,沒有語言的注視總是盼著語言將之說出;在沒有語言的注視,生命與奧祕同時存在,也隨著生命消逝;於是,注視的眼睛開始咿呀學語,語言不能代替注視,而是一種相依偎,與任何身體的感受在一起,而不是互相取代。
同樣地,人是在生死難處的身體處境,召喚了語言作為安慰:有了語言相伴的肉體,彷彿有了依靠;此時的語言並不需要是整段的文字,只需要一些咿呀之詞。這個語言初始的狀態,正是心靈史要重返的地方,而不是歷史的文字。
神話思維正是語言的初始狀態:這種思維是以「感同身受」的方式出現,而不是理性與邏輯。它沒有文字的魔咒,卻有著生命的蘊味;神話思維總是在概念形成之前活著,而在概念形成之後死亡;文明是由理性文字所豢養著,並且驅逐概念之前的神話思維。
因此,重返神話思維的歷史救濟並不是從神話尋求意義結構,而是返回神話曾經居停之處:當我們坐在黑夜星光底下,注視著黑色的山巒,在沒有文字指引之前,我會用眼睛看盡所有的星空與山巒,它們有幾百種不同的黑藍色;可是,在我學會語言之後,我可以用天文學的知識把天空瞄一下,我就把眼前的星空「解釋光了」(explain away);我只消用幾個字,就把眼前的山巒說完了。我學習的文字,讓我對世界失去了興趣,也失去了眼光。
何況,這只是談眼睛的看,若進一步把人與人的面對面接觸當作生命的光景,那番景象當然變得更複雜;人間的生離死別、親情與倫理、政治與經濟,在現代的工商世代經歷數千年的文明歷練,有著非常繁複的系統在運作著,從歷史救濟的觀點來看,如何創造性地對待這些制式的文明,正是所有的知識所欲探求的。若單就心靈史的觀點來看,我們正面臨著制式精神的折磨:一方面我們承受著既成的文字與制度的養育,另一方面又被隔離在生命旨趣之外。
以迷惑為起點,領會「巫」的世界
以語言的制式發展來說,詩意原本是語言與生命交感的處所,但是,制式的語言不斷地朝向工具性或指示語發展,人們只能把語言當作工具,而把語言的生命感掏空了。人們對語言之前的經驗遺忘了,而以語言的器用以及由理性錘鍊的語言反過來詆毀詩意及神話思維。
其中最受殘害的則是有關「巫」的現象。「巫」原本是人類在受苦經驗裡企求解脫的一種基本現象;從文明建立以來,巫被制度化成為祭師或巫祝,從而被取消了巫的根本生命現象;但是,全世界依舊有巫的原始風味存在,只是它的意義被解釋為落伍過時的迷信,或者是人類精神狂妄的非理性殘餘──這是個相當錯誤的觀念,但是二十世紀的人文社會學界逐漸領悟到,人類對自己的生命已經化約成「運動保健與醫療」,對於生命自身的精神豐腴已經逐漸遠離。
把巫現象當作心靈史的歷史救濟,具體言之,就是把我們眼前所理解世界的方式加以質疑,並學習另外一種(或多種)理解世界的方式,使我們領會到我們如何受制於眼前的世界,而深深地感覺到某種缺乏;同時也因此而解開眼前世界所提供的限制,進入一個更豐富的世界。
為了闡明這點,我們把卡斯塔尼達所著的《巫士唐望的世界》當作解說的實例。閱讀卡氏的唐望書必須有個閱讀的起點:我們不可以把卡氏的書當作指引,以為他所說的唐望世界有什麼行為的圭臬可供奉行;相反地,我們必須把自己放在領會的中心,將我們的迷惑當作起點:我到底如何被眼前的世界捕獲而無法解放?
我們的迷惑也許與卡斯塔尼達不完全相同,但是我們之間依稀有著相連之處;我們活在一個「工具理性」的世代,我們為了使生活過得順利,必須把世界看成一個工具性的世界,就像卡氏為了完成他的人類學博士論文,他要有個「資料提供者」當作完成這個目的的人。
他找到印第安巫士唐望,告訴他:「我付你錢,你告訴我有關印第安人藥草的知識。」唐望不吃這一套「工具理性」,他要教導卡氏一個重見世界的方法。唐望行事的方式激怒了卡氏,這不是他要的,他要的是「工具理性」,而這正是唐望教誨的起點,因此,唐望告訴卡氏:「我們之間,總有一個人要改變。」
我們總是以為,被改變的人是下等人,改變別人的人是佔優勢的;然而,從另外的一個世界來看,改變別人對自己並不能蒙受恩惠,願意改變他人並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施行「大慈悲法」,而受改變的是「蒙受慈悲」。當然,在俗世的利益來看,改變他人是為了得益自身,顯然是自私的;但是,若是改變並非得益自身,則是施行慈悲。這兩個觀點都可能存在,唐望則要卡氏看到,他們之間的施受是在「大慈悲」世界的脈絡,而不是卡氏的「爭勝」世界。
然而,卡氏「爭勝世界」的習氣一直使他對唐望有著怒不可遏的生氣,他懷疑唐望是個狡猾奸詐的人。在卡氏原本的世界裡,他所有的懷疑可能都是事實;在俗世裡,我們會碰到偽善的君子、詐財的宗教家,因為我們活在同一個世界。問題是,唐望不在我們俗世的現實,唐望活著的「處所」與「時間」都不在我們這裡,他的處所是我們看不見的:「與植物說話,與動物共存」,他的時間是自然的時間:星光、沙漠、樹叢──這些並不是物質的,而是精神的。
我們與唐望同樣擁有星光、植物與動物,但是卻採取不同的方式:動物是超市裡的畜肉或寵物店的可愛動物,植物是「菜餚」與「觀賞物」,時間是「工作」與「休閒」……。換句話說,我們的文明創造了世界的秩序,但卻也遮蔽了唐望知道的世界。
做野地的獵人,而非有知識的瞎子
心靈的歷史救濟就是在於重新挖開被我們掩蓋的東西──或許我們的祖先曾經活在那裡,並得到某種真理,但是我們因為某種緣故,將之忽視了,以致當歷史文明往前走了之後,這些真理被隱藏起來,直到我們發現有人依舊在那裡活著。
這樣的重新回頭,對人類的精神發展史有莫大的激勵。以「與植物說話」為例,我們與卡氏一樣,認為這是很荒謬的事,頂多是用「開玩笑」的方式來做,即使有人發現,「與植物說話」可以讓植物長得更好,這也是功利式的,與唐望的心靈世界完全沒有關係。
我們並不需要把唐望視為什麼偉大的人,他只是站在我們曾經失落的世界說話;他是我們世界的提醒者,提醒我們曾經有過一種世界,這個世界不是滅絕,而是讓我們重新去接壤。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如何與「唐望書」接壤:它既不是提供有關能量?能源的理論,也不是提供某種比喻式的格言,更不是提供真理,而是提供一個位置──我們失去的位置。
這個位置就在「巫現象」裡頭。「巫現象」的真正意思就是「初始經驗」──第一次的經驗,也就是佛教所謂的「初心」:
你必須抹去周圍的一切事物,直到沒有一件事是理所當然的,沒有一件事是確定的……(卡氏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紀錄)
與文明或文化相較,「巫現象」沒有精確的語言,沒有制式的習氣,更沒有一成不變的規律。「巫現象」不是巫術,也不是儀式,而是擺脫被文明或文化豢養的束縛,直接把自己置身於「野地」。「野地」是精神的,意味著人必須在生死之間搏鬥,它是行動的處所,人必須小心翼翼地求生存,機敏地保護自己,並且尋求活下去的力量,但也必須與萬物俱亡。與之相較,文明或文化的生活是一個被養在豬欄裡的生活,照著習性的制約,每天三餐,把身體交給醫療保健機構,把生活策略交給專家,依照書本的教條行事,只憑報紙及電視「增長知識」,也就是把整個生命交給文化來殖民。
當唐望把卡氏帶到野處,卡氏是個「有知識的瞎子」,他看不見野處的一切,聽不懂野處的語言(如「好地」、「壞地」、精靈、風、石頭),他軟弱無力,不認識「力量」,不會「正確的」走路,而「野地」需要的是「成為獵人」──這並不是寓喻,而是一種解開被文明或文化豢養的行動。
在野地的實景就是我們的「生死場」,我們的左邊是出其不意的死亡,我們的右邊是眼前的世界;我們的前面是難以到達的遠景,我們的後邊是個人歷史的習性;在整個唐望的教誨裡,我們必須以身陷野地的膽識,往左看一看死亡,往右偵伺我們的世界;眼前迷茫的一片是我們必須小心翼翼的探索之地,而背後的個人歷史就必須擺脫,以免難以移動。
如果返回現代世界來看,事情是獵物,現代的獵人是行事機敏的人;被現代豢養的人是那些被工作、電視、電腦與餐館包圍起來的人,時間被分割成週一到週六,朝八晚五,但是驚覺的人懂得人的精神裡有「野地」,他懂得進入名利場,也同時把名利擺開,有一種依賴自身的求生能力,但也懂得接受死亡。
心靈的歷史救濟,解放日常生活殖民化
談「巫」,必須認識到人類在受苦的經驗所進入的世界:一種解脫狀態的迷離,一種人類生命造景的力量;所有的「巫」現象,在還沒有進入制式化之前,都把人的苦難與生死的感受以各種舞蹈、虛擬實境的方式,為人類的精神領域指明一條生路。卡斯塔尼達的唐望書,乃至赫塞的《流浪者之歌》都以同樣的方式,向人類的肉體受難處境,指出一片景象。
然而,「巫」現象永遠只是「指出景象」,而不是累積的知識──一旦「巫現象」成為知識,或為巫醫,或為巫官,或為巫術,都變成虛假的知識。「巫」現象自身是生命的處境,本質上是人類命運劫數的無明。它總是透過一些受苦的人把生命景象的光透露出來,因而讓人明白生命的暗處;對於「巫」現象,也不是信或不信的問題,而是人如何解除文明的遮蔽,(而)願意自我揭露生命奧祕的問題。
對於理性,巫現象的存在是個令人尷尬又極力排斥的存有狀態,但是,對心靈史的歷史救濟而言,既是生命的存有狀態,我們必須回到現象自身。
同樣地,神話思維也不在於神話象徵的解讀,更不是神話的想像,而是對語言魔力回到生命的再度思維:人與大地的關係(如西雅圖酋長的話),人與植物、動物共依存的關係,人與方位、時間的關係,人的生殖、親情乃至情色的思維。神話思維必須擺脫文字理性的宰制,使得生命與語言之間的原初處境得以再次被揭露。在這一方面,文化現象學者卡西勒的《神話思維》、神話學者坎伯的系列著作,乃至保羅?呂格爾的《惡的象徵》,都致力於神話思維的歷史救濟工作。
前述心靈史的歷史救濟中,只稍微談到巫現象與神話思維,若從宏觀的歷史實踐觀點,不管是德國社會學者哈伯瑪斯的「日常生活殖民化」的解放,政治學者漢娜?鄂蘭的「失去世界」的復歸,哲學家海德格、尼采的生命哲學,都是朝著歷史救濟的觀點,對現代人文社會的異化(疏離)提出反抗。
|